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,文化既是传承千年的精神基因,也是驱动发展的核心动能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“乡村振兴需以文化铸魂”,而《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》则进一步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纳入国家战略框架。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,不仅包括农耕文明、民俗传统等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,更需通过文化产业这一引擎实现活化与增值。这种“赋能”既是对乡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,也是以市场机制激活文化生产力、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系统工程,其本质在于通过产业化的路径,让乡村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动态发展,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。
农耕文化:乡村振兴的根基
农耕文化是乡村文明的底层密码,其内涵涵盖生产工具、耕作技术、民俗节庆等多元维度。从贵州“村BA”篮球赛的火爆到台盘乡“喜柿礼堂”的文旅融合实践,这些现象背后均折射出农耕文化中集体记忆与地域特色的生命力。例如,传统农事节日通过现代节庆活动的重构,既保留了“二十四节气”的时间智慧,又衍生出旅游、研学等新型消费场景。
当前农耕文化开发仍面临无序性与同质化挑战。如所述,部分地区存在“竭泽而渔”式开发,导致文化符号过度商业化。系统性保护成为关键:一方面需建立资源名录与保护条例,对梯田景观、传统农具等物质载体进行分类建档;另一方面需依托村规民约设立开发边界,如浙江松阳县通过“拯救老屋行动”实现古村落保护与文创产业的平衡。这种“保护性开发”模式,使农耕文化既能维系乡土认同,又能转化为差异化竞争优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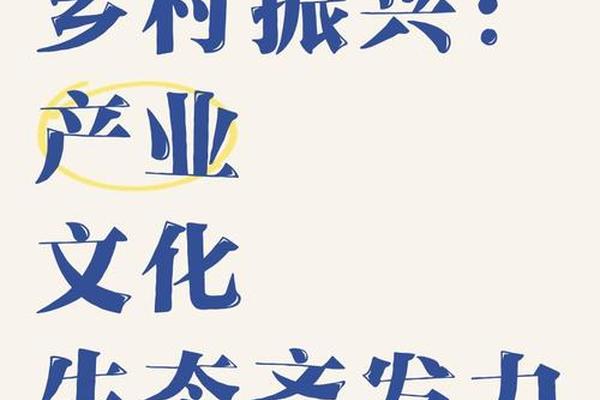
文化产业:城乡互融的引擎
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逻辑,在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价值跃升。《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》提出八大重点领域,包括创意设计、音乐产业、数字文化等。例如,安徽宏村将徽派建筑美学融入旅游IP,年接待游客超百万;贵州丹寨以苗族蜡染技艺为核心,构建“非遗+电商”产业链,带动数千农户增收。这些案例印证了“文化资源—产品创新—产业增值”的转化路径。
这一过程中,“沉浸式体验”成为关键突破口。日本濑户内国际艺术节通过在地艺术装置激活衰败乡村,中国武家泥塑则探索“非遗+教育”模式,将传统技艺转化为研学课程。此类实践不仅打破文化展示的静态局限,更通过互动性消费增强用户黏性。数据显示,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“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”,要求各地培育“文化+生态+产业”特色品牌,这为文化产业与乡村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。
人才培育:文化振兴的关键
乡土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。当前乡村普遍面临“空心化”困境,而指出,需构建“选拔—培训—激励”的全链条机制。例如,费县通过“美在农家”门牌评选、手工艺培训等方式,培育本土文化能人38000余名;内蒙古阿尔山西口村则引入艺术家驻村计划,以“外脑”激活传统墙绘艺术。这种“内生+外引”的双轨模式,既能保留文化原真性,又注入创新基因。
高校与企业的参与进一步拓宽人才渠道。清华大学文创研究院推动“乡创”理念,鼓励青年设计师扎根乡村;而对外经贸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在2025年寒假调研中,探索“电商+文化IP”的创业模式,为37个乡村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。此类实践表明,人才培育需打破学历与地域限制,构建、高校、企业联动的“人才飞地”。
公共文化:普惠服务的重构
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长期存在供需错位问题。传统“送戏下乡”等单向供给模式难以满足多元需求,而提及的“柔性供给机制”提供新思路:通过大数据分析村民偏好,定制“戏曲进乡村”“非遗工坊”等项目。例如,湖南中鱼口镇建立“文化资源直达机制”,将图书馆、影剧院等设施与本地傩戏展演结合,参与率提升60%。
政策创新亦不可或缺。2023年《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方案》要求试点县市优化资源配置,如浙江安吉通过“生态文化券”制度,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设施建设。此类探索将主导转变为“搭台、市场唱戏”,使公共文化服务从“有没有”转向“好不好”。
创新转化:动态发展的路径
文化振兴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创新转化能力。一方面需挖掘文化符号的当代价值,如“村BA”将篮球运动与苗族芦笙节结合,衍生出体育旅游新业态;另一方面需借助科技手段突破时空限制,如江西蒋沙渔村通过VR技术复原古代渔猎场景,吸引年轻消费群体。
未来方向可聚焦两点:一是构建数字化文化基因库,利用区块链技术对非遗技艺进行确权与传播;二是探索“文化跨境”路径,借鉴西班牙葡萄酒主题游经验,推动中国乡村文化IP走向国际。正如北川富朗所言:“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创造新价值”,唯有持续创新,方能实现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共荣。
从文化自觉到振兴自觉
乡村文化振兴的本质,是通过载体建设与产业赋能的双向互动,重构乡土文明的价值体系。农耕文化的系统性保护、文化产业的创新性转化、人才梯队的结构性培育、公共服务的普惠性提升,共同构成这一进程的支柱。当前,政策层面已形成从中央文件到地方试点的完整框架,而实践层面仍需在标准化与特色化之间寻求平衡。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文化资源资本化的量化模型,或比较不同区域赋能路径的效能差异,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理论工具。当文化不再是被凝视的“他者”,而是驱动发展的主体,乡村振兴方能真正实现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深层目标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