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图景中,乡土文化能人如同根系深扎的榕树,既承载着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,又萌发着现代文明的新芽。他们既是传统技艺的守护者,也是乡村变革的推动者,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中构筑起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桥梁。从“村晚”舞台上的民间艺人到田间直播的“新农人”,从非遗工坊的匠人到乡土教育的实践者,这些活跃在基层的文化实践者正以独特方式重塑乡村文化生态,为千年农耕文明注入时代活力。
定义与多维属性
乡土文化能人特指扎根农村基层,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群体。根据中央《“十四五”文化发展规划》的界定,其涵盖工艺美术、表演艺术、文化传承等七大类别,既包括掌握木雕、刺绣等传统技艺的民间工匠,也包含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乡土美学的青年创作者。这类群体具有双重属性:在文化维度上,他们是活态的文化基因库,通过口传心授保存着村规民约、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;在社会维度上,他们充当着文化治理的柔性力量,能够通过道德示范、技艺传承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,增强社区凝聚力。
这种身份的特殊性源于其文化根脉的在地性。如费孝通所言,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,即便在城镇化率达65%的今天,超过5亿农村常住人口的文化认同仍深植于土地。陕西凤翔泥塑传承人胡新明家族六代坚守技艺传承,同时创办合作社带动200余户村民增收的案例证明,乡土文化能人正是这种“在地性”与“现代性”的完美结合体。
乡村振兴中的核心功能
在经济振兴层面,乡土文化能人发挥着产业催化作用。河北武强县通过“公司+非遗工坊”模式,将年画技艺转化为年产值超2亿元的文化产业,带动全县建立32个专业合作社。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实体产品上,更表现为文化资源的数字化重构。河南叶县“山水常村”电商直播基地培养的乡土主播,通过短视频日均销售农产品5000单,创造性地将田间劳作转化为文化展演。
文化传承方面,他们架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桥梁。贵州榕江“村超”赛事中,侗族大歌与足球竞技的融合展演,使古老歌谣获得亿万次网络传播。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的形式嫁接,而是如学者王克修指出的“内生智慧与创意设计的有机融合”,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同时拓展传播边界。
社会治理功能则体现在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过程中。四川泸州的田野调查显示,具有威望的乡贤通过调解纠纷、组织民俗活动,能使基层矛盾化解效率提升40%。这种非制度化的治理方式,恰是《乡土中国》所述“礼治秩序”的当代延续,在法治框架下形成有效的治理补充。

培育机制与路径创新
政策体系的构建为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。国家文物局推动的“传统村落保护工程”,五年间修复古建筑2.4万处,同步培育出3.7万名古建修缮技工。农业农村部实施的“先锋计划”,则通过数字技术培训,在72个县域培育出既懂农业生产又擅新媒体运营的复合型人才。
培育模式的创新体现在三个维度:一是“产学研”融合,如江西黎川油画产业基地与中央美院合作,既传承传统瓷板画技艺,又培养出500余名现代艺术创作者;二是数字赋能,浙江乌镇建立乡村数字文化馆,利用VR技术开展非遗沉浸式教学;三是社群激活,山西五村通过“播种节”等民俗活动,使普通村民转化为文化传播节点。
人才吸引机制突破城乡壁垒。政策创新方面,江苏昆山试点“乡村人才公寓”制度,为返乡青年提供三年免租创业空间;市场驱动方面,云南“乡土公社”平台吸引2000余名城市设计师参与乡村文创开发,形成城乡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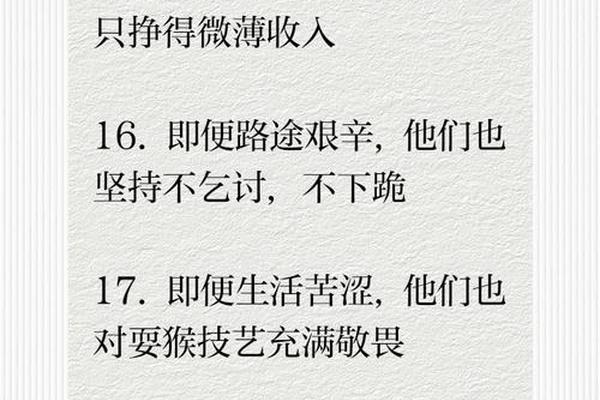
现实挑战与发展对策
当前培育体系面临三重困境:人才断层危机(60岁以上非遗传承人占比达58%)、知识更新滞后(仅12%的乡土能人接受过系统培训)、评价机制缺失(79%的县市缺乏文化人才认证标准)。破解之道需多方协同:在法律层面加快《乡土文化保护法》立法进程,确立技艺传承人的社会地位;在教育层面构建“县域职业院校+大师工作室”的二元培训体系;在技术层面推广腾讯“数字乡民”计划,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化确权与价值转化。
未来研究应聚焦三个方向: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机制、数字技术对乡土认同的重构效应、城乡文化要素的流动模型。如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近年开展的“数字乡愁”项目,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建立200个传统村落数字档案,为文化传承提供新思路。
站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节点回望,乡土文化能人群体恰似文化DNA中的双螺旋结构——既保持着传统文化的稳定性,又具备与现代文明结合的突变能力。他们的实践表明,乡村文化振兴不是简单的遗产保存,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构建新的意义系统。当青年创客用无人机拍摄梯田春耕、当银发匠人在直播间展示榫卯技艺,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,正在书写着一部属于21世纪的中国乡村文明演进史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