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日的蝉鸣裹着热浪涌进老屋的窗棂,檐角铜铃轻响,奶奶从褪了漆的木柜中取出一个青布包裹,层层展开后,露出一柄泛着幽光的竹制漆扇。扇骨上斑驳的朱红与墨黑交错,仿佛凝固了千年的时光。那一刻,漆艺的芬芳裹挟着岁月的气息,在我心底悄然生根。
一、初识漆艺:笨拙中的敬畏
奶奶是镇上最后的漆艺匠人,她总说:“漆是活的,要用心去养。”第一次学制漆扇时,我执笔沾漆,却在竹骨上晕开一团混沌。奶奶不恼,只让我将扇面浸入山泉,看漆色随水纹舒展,化作一尾游动的锦鲤。“漆要七分静气,三分灵动。”她指尖轻点,教我如何以松针蘸漆勾勒鳞片,又用金粉填彩。我屏息凝神,却总在收尾时抖落金箔,惹得她笑叹:“心不静,漆便不听话。”
那些午后,我常在老屋的阴翳里听漆液滴落的声音。奶奶说,漆树的眼泪要经三伏三九才能凝成琥珀般的膏体,正如匠人的手艺需千锤百炼。她翻出祖传的漆器图谱,指着宋代《髹饰录》中的纹样道:“这云雷纹是老祖宗与天地对话的密码。”我抚摸着扇面上凹凸的纹路,忽然懂了为何漆艺能跨越千年——每一道纹都是匠人与自然的私语,每一抹色都是光阴沉淀的秘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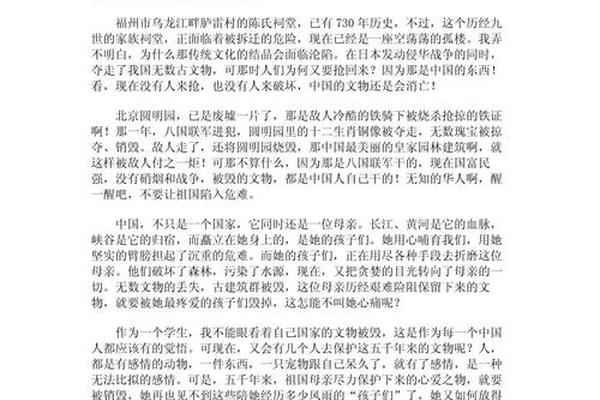
二、破茧之痛:传统与创新的碰撞
高中社团展演前,我想用漆扇创作现代题材。熬夜设计的赛博朋克纹样却被奶奶否决:“漆艺不是画布,要守它的筋骨。”争执中,扇骨被我失手折断,漆液泼溅染脏了设计稿。那一夜,奶奶默默修补断骨,用螺钿嵌出星辰轨迹:“老手艺不是枷锁,是根。根扎得深,新芽才能长得旺。”
我重新提笔,将北斗七星化入漆纹,以银粉勾连成星座网络,又在扇柄镌刻二维码,扫码可闻漆艺故事。展览当天,漆扇在玻璃展柜中流转光华,有观众惊叹:“古漆竟能映出未来!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刻旧物,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的呼吸里。正如《黑神话·悟空》用游戏重述西游,漆艺亦能在创新中焕发新生。
三、薪火相传:方寸之间的文明接力
高考前夕,我带着漆扇参加非遗文化节。展台前,一群孩童踮脚追问:“姐姐,漆树会疼吗?”我学奶奶当年的样子,将他们的指尖轻触扇面:“漆树割浆像枫树流泪,匠人取之有度,百年后又是一棵好树。”一个小女孩用彩笔在纸上摹画漆纹,歪斜的线条竟与我的初学之作惊人相似。
离乡求学时,奶奶将祖传漆刀递给我:“老手艺不能断在机器流水线上。”如今,我在大学组建漆艺社,带同学用丙烯颜料模拟大漆质感,以3D打印辅助制胎。有人质疑这是妥协,我却想起敦煌壁画中的异域飞天——文明因交融而瑰丽。我们以直播展示漆扇制作,弹幕里闪过无数“原来传统文化这么酷”,屏幕外的我仿佛看见千百年前,丝绸之路上漆器与胡琴共奏的盛景。
后记
一柄漆扇,不过方寸,却凝着山河岁月的倒影。从奶奶的老屋到都市的展台,从松针蘸漆到数字建模,变的只是载体,不变的是漆液中沉淀的敬畏与匠心。当我们以青春为笔,为传统续写新章,便是对文明最深情的告白。正如《只此青绿》让丹青起舞,漆艺的芬芳,终将在新一代的手中绵延千年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