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资源作为人类文明积淀的核心载体,既包含物质形态的历史遗存,也涵盖非物质形态的精神传统与生态景观。向勇(2015)指出,特色文化资源具有“物质形态、非物质形态与自然文化资源”三重属性。以中国为例,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、昆曲的唱腔程式、张家界的喀斯特地貌,分别对应了文化资源的物质性、非物质性与自然性特征。这种多元形态的资源禀赋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要素,例如贵州依托“红色文化+数字技术”打造的《红飘带·伟大征程》沉浸式演出,正是将革命历史资源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典范。
从全球视野看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体系将文化资源分为文化遗产、自然遗产与文化景观三类,这种分类方式凸显了文化资源的复合价值。牛淑萍(2012)在《文化资源学》中进一步提出,文化资源的功能不仅限于审美体验,更承载着“社会凝聚力培育、经济价值转化与生态保护协同”的复合使命。例如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通过采集3万条工艺数据,既保存了传统制瓷技艺,又为现代文创产品开发提供数据支撑,实现了保护与开发的动态平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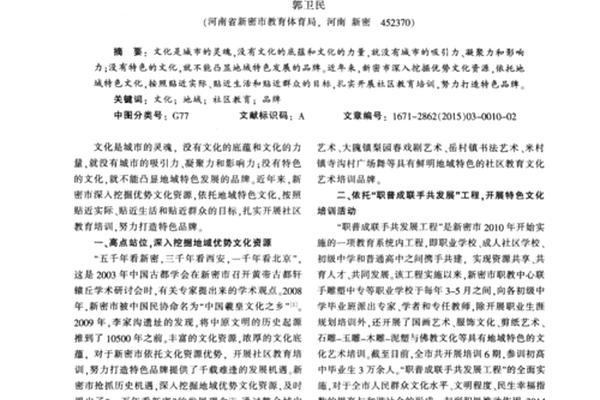
价值评估体系的科学构建
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需以科学评估为前提。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构建的“双维度评估模型”具有重要参考价值:该体系从人文价值(奇特价值、传承价值等6项指标)与经济价值(规模价值、带动价值等6项指标)两个维度,构建包含36项三级指标的评估矩阵。例如对丽江古城的评估发现,其“认同价值”指标中“外地人推介意愿”得分高达9.2(满分10),这直接支撑了其文旅IP的市场转化率。
在定量分析层面,赵淼(2024)提出的“文化新质生产力”概念强调数据要素的关键作用。贵州通过建立民族文化大数据平台,对苗绣纹样进行数字化解构,使传统工艺的现代转化效率提升40%。这种评估方法突破传统定性分析的局限,正如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评估》研究所证实的:当文化资源价值被量化为“每公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”时,其空间规划决策支持效能可提升57%。
开发模式的创新路径
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多元主体协同。安阳师范学院构建的“1232”模式具有示范意义:通过整合红旗渠精神与甲骨文资源,开发出《红旗渠精神虚拟仿真实验》等数字化课程,实现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双向赋能。这种“文化基因+科技载体”的开发路径,使学习者参与度从传统教学的32%提升至89%。
在产业化实践中,“嵌入式开发”成为新兴趋势。景德镇将古窑遗址改造为陶艺创客空间,吸引200余家文创企业入驻,形成“历史场景—创意生产—消费体验”的闭环生态。这与民建中央(2025)提出的“融合式文化空间”理念高度契合,即通过“文化空间功能复合化”使单位面积文化产值提升3-5倍。
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索
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需建立保护与开发的动态平衡机制。荆州文保中心研发的“简牍脱色脱水工艺”,使2000年前秦汉简牍的完整保存率从60%提升至95%,这种技术创新为脆弱性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奠定基础。《民间文化资源可持续开发》研究强调社区参与的不可或缺性:云南扎染技艺通过“传承人+合作社+电商平台”模式,既保证技艺原真性,又使从业者年均收入增加2.4万元。
在政策层面,许唯临(2025)提出的“革命文物活化利用”策略具有启示性。延安通过AR技术重现枣园会议场景,使游客停留时间从1.2小时延长至3.5小时,衍生品收入占比达总营收的38%。这种“科技赋能+内容深耕”的双轮驱动,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“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保护”的重要论断。
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
文化资源优势的深度释放需要构建新型生产关系。建议从三方面突破:其一,建立“文化资源资产评估国家标准”,借鉴《文化资源价值评估导则》研究成果,制定涵盖知识产权、生态补偿的量化体系;其二,培育文化数据要素市场,如建立区域性非遗数字交易平台,破解“资源—资本—资产”转化梗阻;其三,创新文化金融工具,试点“文化遗产信托基金”,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保护性开发。
全球化语境下,文化资源的竞争优势更需彰显主体性。故宫博物院通过“数字文物库”开放7.5万件藏品数据,吸引全球开发者创作5.6万款数字产品,这种“开放资源—集聚创意—价值裂变”的模式,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新范式。正如余惠芬(2017)所述,文化外交的深层逻辑在于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”,这需要我们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探索文化现代化的中国路径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