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仕强教授将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归结于《易经》,认为其“一动分阴阳”的哲学体系构成了华夏文明的核心框架。他指出,《易经》不仅是群经之首,更是中国人宇宙观、人生观与方法论的根源,其“一画开天”的创世逻辑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。在《中华文化的特质》中,他阐释道:“太极即‘中’,未发为体,已发为用,阴阳交感而生万物,这种动态平衡的思维贯穿于儒道法各家思想中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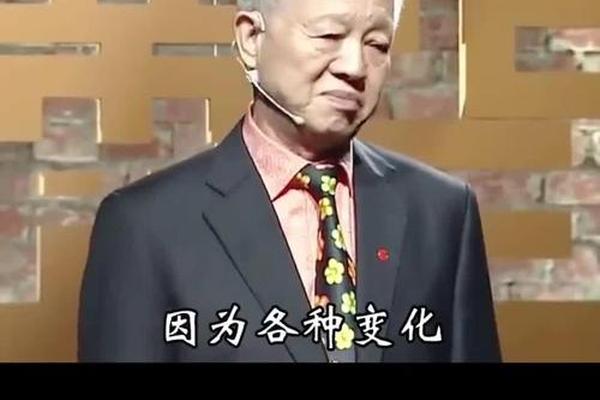
这种文化根基具体表现为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曾仕强以《道德经》为例,强调“道法自然”不是被动顺应,而是通过“推己及人”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。他曾在洛阳考察时指出,河洛文化中的“汤汤水水”与闽南饮食习俗的关联,印证了中华文化“大同不灭”的传承特性。这种以《易经》为纽带的文化认同,使得中华文明虽经历朝代更迭,仍能保持内核的稳定性与包容性。
二、文化特质的思维密码
曾仕强提炼出中国式思维的两大核心特质:阴阳辩证与合理即中。他认为中国人擅长“从现象看本质”,如通过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成败剖析“时势造英雄”的规律,这种思维方式源自《易经》的变易哲学。他强调:“合理即中,但这个‘理’是动态的,需因时、因地、因人调整。”

在具体实践中,这种思维体现为“集体智慧”的决策模式。相较于西方的个人主义,中国人更注重“商量着办”,正如他在《中国式管理》中所言:“领导者的最高境界是让团队自发形成共识。”这种思维特质也反映在语言艺术中,曾仕强常提醒学生要“听出弦外之音”,因为中国人讲究“点到为止”,这与西方直白表达形成鲜明对比。
三、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
面对全球化冲击,曾仕强提出“创新不忘本”的转型路径。他创办的罗浮山泰学学校,将《易经》与数学、音乐课程融合,开发“易经大富翁”等教具,使“不易”的智慧以“变易”的形式传承。这种实践印证了他的观点: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复古,而是“用中国人的方法解决中国人的问题”。
在管理学领域,他开创的“中国式管理”理论颠覆了西方范式。通过比较中美日管理模式,他发现中国人更注重“情理法”的次序,管理者需具备“圆通而不圆滑”的智慧。这种理论在华为等企业的实践中得到验证,印证了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东方管理哲学。
四、文化传承的动态演进
曾仕强将文化比作“自然演化的河流”,强调传承需兼顾“经”与“权”。他认为,《孝经》所载的礼仪规范是“经”,而具体实践中的孝道表达则是“权”。在家庭教育中,他主张“六斤米”课程,通过让孩子为父母背米体验孝心,使抽象转化为具身认知。
这种动态性还体现在他对“家风”的解读中。在《家风:传统文化的传承》里,他提出“家规要随时代调整,但孝悌精神永不褪色”。他建议现代家庭建立“家族日志”,通过记录日常互动培养代际间的文化默契,这种创新方法使古老智慧焕发新生。
五、文化价值的全球对话
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,曾仕强预言“21世纪是中国式思维的时代”。他对比中西文化差异:西方管理强调制度刚性,中国智慧注重弹性应变;西方宗教易引发冲突,而儒释道却能和谐共生。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特质,恰是化解文明冲突的关键。
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春花评价:“曾仕强的理论架起了东西方管理学的桥梁。”他提出的“太极思维管理模式”被哈佛商学院纳入案例库,证明中国智慧能为全球治理提供新范式。这种文化输出不是单向灌输,而是通过“阴阳互济”实现文明互鉴。
曾仕强对中华文化的诠释,构建了一个从《易经》根系生长出的智慧体系。他既守护着“合理即中”的文化基因,又开创出“中国式管理”的现代范式,在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中架起桥梁。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两个方向:其一,数字化时代如何运用AI技术解码《易经》的预测模型;其二,将“孝悌乐群”等传统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组织原则。正如曾仕强临终所言:“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日新又新”,这既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密码,也是其在新时代续写辉煌的必经之路。


